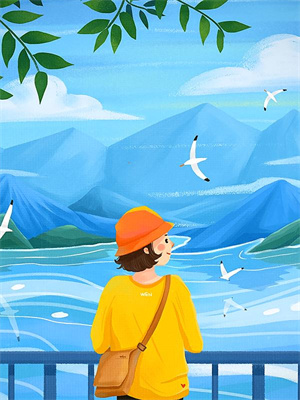简介
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充满奇幻与冒险的历史古代小说,那么《笑谈忠》将是你的不二选择。作者“文野笑长生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何墨唐渊的精彩故事。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,喜欢这类小说的你千万不要错过!
笑谈忠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雁门关的二月,是铁与血淬炼后的沉寂。
去年冬十一月那场饮马河后的血战——史称“雪关之役”的余烬,早已被北风吹散在苍茫雪原。关墙上的刀痕箭孔比三个月前又多了一倍,裸露的夯土层像一道道新旧的伤疤交错,在惨白的春日下格外刺目。积雪顽固地盘踞在关隘阴面,边缘已开始发黑融化,雪水沿着城墙砖缝渗下,夜里又结成薄冰,清晨时分闪着森冷的光。
何墨站在东侧敌楼最高处,左手按着垛口,指尖感受着砖石被风霜侵蚀出的粗糙纹路。
他每日寅时三刻必至此地练剑,已成了守军皆知的习惯。今日天色灰蒙,朔风从关外卷来细碎的雪沫,打在脸上如针尖轻刺。何墨缓缓拔出乌金剑,剑身在晦暗晨光中不反射半点光泽,仿佛能将光都吸进去。剑格处何家的徽记已磨损得只剩轮廓,那是父亲何靖当年亲手刻下的。
十二年了。
何墨闭上眼,还能看见那个雪夜。父亲背着他和妹妹月儿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逃,舒杰紧跟在后,那年舒杰才十二岁,却已懂得用树枝抹去雪地上的脚印。追兵的火把在远处林间晃动,箭矢破空声——
“墨儿,带小杰走!”
何靖将他推给舒杰,转身拔刀。那是何墨最后一次看见父亲的背影,皮甲上插着三支箭,却依然挺得笔直。后来他们在北莽草原当了六年猎户,舒杰总在半夜惊醒,喊着“何叔”。何墨从不哭,只是把弓弦绷得更紧,把刀磨得更锋利。
直到去年,他们返回中原。六月,乌兰死在鬼门道。
直到现在。
何墨睁开眼,剑尖微颤。左肩传来熟悉的滞涩感——呼延灼那一刀留下的旧伤虽已愈合,但筋腱终究不如从前。剑尖划过半圆时,左肩胛骨深处会传来细微的刺痛,像有根生锈的铁丝在血肉里轻轻刮擦。
他早已习惯这种痛楚。就像习惯没有父亲的日子,习惯没有月儿的日子,习惯……满是伤痕的日子。
“哥。”
身后传来声音,很轻,但何墨还是听到了。那是十六年朝夕相处才能辨出的脚步声——舒杰上城楼时总会刻意放轻,怕惊扰他练剑。
何墨收剑归鞘,没回头:“又没睡好?”
舒杰走到他身侧,两人并肩而立。关外是茫茫雪原,饮马河在三十里外,此刻应已开始解冻。去年十一月的雪关之役,何墨率乌衣营死守左翼,舒杰他们却因在长安追查王玹余党,直到战役结束前三天才赶回雁门关。
“昨晚梦见何叔了。”舒杰声音有些沙哑,“还是那个雪夜。”
何墨沉默。半晌,伸手拍了拍舒杰的肩膀——这个动作,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。何靖活着时,总这样拍他们的肩,说“没事,有爹在”。
现在,只剩下他们彼此了。
“你的伤怎么样?”舒杰转头看他,目光落在何墨左肩,“饮马河那战留下的箭伤……”
“好了。”何墨简短道,顿了顿,“你腿上的伤呢?”
“早好了!”舒杰咧嘴笑,露出白牙,“陈巧那丫头天天炖汤,补得我都胖了。”
他确实比三个月前壮实了些。肩膀宽了半寸,手臂肌肉在皮甲下隆起清晰的轮廓。只是眉宇间那股子憨直未变,只是眼底深处多了些东西——那是亲眼见过尸山血海后,少年意气沉淀成的沉稳。还有一丝何墨能看懂的愧疚。
因为错过了饮马河血战,没能和何墨并肩。
“哥,”舒杰忽然低声说,“下次……我一定在。”
何墨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,只是又拍了拍他的肩。
有些话不必说。十六年,从两个孩子蜷在同一个破庙里取暖,到如今并肩站在这天下第一关上,他们是彼此最后的家人。
—
校场在关内西侧,原是一处屯田的晒谷场。
舒杰到时,已有数十新兵在晨练。见他扛戟而来,人群自动让开一片空地,眼中满是崇敬——虽然错过了饮马河,但黄河渡口一战,“舒一戟”的名号已在北境传开。传闻他一人守渡口半个时辰,戟下亡魂不下三十。
“舒校尉!”有新兵抱拳行礼。
舒杰摆摆手,走到场中央。那里立着五根碗口粗的松木桩,是昨日刚埋下的,树皮还带着湿气。
他深吸一口气,脑海中却闪过何墨独上城楼的背影。
那背影太像何叔了。一样的挺直,一样的孤独。
方天画戟在手中转了个圆,戟刃破空发出低沉的嗡鸣。舒杰右腿后撤半步,腰身如弓弦般绷紧——然后猛然发力!
没有花哨的招式,只是何靖当年教的最基础劈砍。那个糙汉子不会什么高深武学,只说“力气大,就往死里砸;力气小,就往要害扎”。
“咔嚓——!!!”
三根木桩应声而断。断口整齐如刀切豆腐,木屑炸开,溅出三丈远。剩下两根木桩被余势震得剧烈摇晃,埋土处裂开细纹。
全场寂静。
舒杰收戟,气息平稳如常。三十八斤的画戟在他手中轻若灯草。他看了看断桩,皱眉嘀咕:“还得收三分力,不然木桩不够用……”
新兵们这才哗然。
“三根!一戟劈断三根!”
“这要是劈在人身上……”
舒杰挠挠头,有些不好意思地冲众人笑笑。转身时,看见陈巧站在场边,手里捧着个粗陶碗。
这丫头正式从军后换了装束,一身合体的皮制轻甲,头发梳成利落的单髻。只是那双眼睛依旧灵动机警,走路时脚步轻得几乎无声——踏燕步的底子还在。她来雁门关不过四个月,却已成了侦缉队长,领三十名机灵士卒。
“舒杰,趁热。”陈巧把碗递过来,眼睛却瞟向别处。
舒杰接过,是羊肉汤,撒了葱花和胡椒。汤熬得奶白,肉块炖得酥烂。他咧嘴一笑,咕咚咕咚几口喝干,抹抹嘴:“好喝!比军灶的强多了。”
“我加了当归和黄芪,李医官说对伤口好。”陈巧接过空碗,指尖不小心碰到舒杰的手,立刻缩回去,耳根微红。
舒杰没察觉,自顾自说:“你那侦缉队今日出关不?”
“要出。探到北莽斥候在五十里外的野狼坡活动,得去摸摸底。”陈巧说着,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,“这个你带着。”
舒杰打开,是三个油纸包。一包肉干,一包止血散,一包……糖渍梅子。
“路上馋了吃。”陈巧说完转身就走,脚步匆匆,像怕他问什么。
舒杰看着她的背影,愣了片刻。这丫头是去年还是个小贼。一路跟着他们回雁门关,不知不觉就成了……成了什么?舒杰说不清,只是看见她,心里就踏实。
就像看见何墨,就像想起何叔。
他把布包仔细塞进怀里,贴着胸口放好。那里还有一枚旧铜钱,是何靖当年给他们的——一人一枚,说“将来娶媳妇用”。何墨那枚大概早就丢了,舒杰这枚却一直留着,铜锈都磨亮了。
—
中军帐内,炭火烧得正旺。
唐渊坐在长案后,面前堆着两摞半尺高的文书。他换了身深青色的文官常服,袖口已磨得发毛——监军御史的绯袍太显眼,在军营里反而不便。
笔尖在砚台里蘸饱墨,却悬在半空迟迟未落。
他目光落在案角那封信上。江南来的信,用的是润州特产的浣花笺。信已读了五遍,蒲英儿说三月粮草已备齐,正发往太原府。末了添了句:“闻君安好,英儿心稍慰。雁门苦寒,万望珍重。”
唐渊提笔回信,写了几行又停。
帐帘掀开,杨万走了进来。
他比三个月前更瘦了,颧骨凸起,眼窝深陷。左手蜷在身侧,手指不自然地弯曲。右臂因代偿性训练粗壮了些,但整体依然单薄,披着甲都显得空荡。
“唐兄。”杨万声音沙哑。
唐渊起身:“怎么不多休息?李将军不是准你休养到月底?”
杨万摇头,走到沙盘前。沙盘上,鹰愁涧的位置插着一面小蓝旗。
“我要守这里。”他说,语气没有商量余地。
唐渊走到他身侧。鹰愁涧地形险要,形如鹰嘴合拢,仅容三马并行。确是易守难攻之地,但……
“你左手不便,若敌军攀崖——”
“所以我要弩手。”杨万打断他,“两千弩手,五百刀盾。够了。”
唐渊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曾清澈如草原湖泊,如今却沉寂如深潭。乌兰死后,杨万就变成了这样——话更少,眼神更冷,只是偶尔擦拭那枚银铃时,会露出一瞬恍惚。
“李将军同意了吗?”唐渊问。
“我会让他同意。”杨万说,顿了顿,“乌兰说过……想看看中原的春天。”
他没再说下去,转身走了。皮靴踏在青石地上,发出沉闷的回响。
唐渊坐回案前,却再也写不下去。他想起去年六月,鬼门道那个雨夜。她看了杨万最后一眼,嘴唇动了动,没发出声音。
但他们都看懂了。
“活下去。”
帐外传来亲兵通报:“唐大人,李将军有请。”
唐渊收好信纸,起身时右肋传来轻微刺痛——那是黄河渡口留下的刀伤。他披上大氅出帐,二月寒风扑面,不由得紧了紧衣领。
李牧的帅帐前,那两尊前朝石狮子依旧沉默。
进去时,老将军正站在沙盘前,手里捏着几面小旗。见唐渊进来,指了指鹰愁涧:“杨万来过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怎么看?”
唐渊沉默片刻:“下官以为……可以让他试试。”
李牧抬眼看他。
“杨校尉需要证明自己。”唐渊继续说,“不是向我们证明,是向他自己。乌兰姑娘的死……他背了太重的担子。守鹰愁涧,或许是让他走出来的路。”
李牧叹息,将蓝旗插稳:“那就给他两千五。但你要保证后勤,箭矢、火油、药品,优先供应鹰愁涧。”
“是。”
老将军走到窗边,望向校场方向。那里传来舒杰练戟的呼喝声,沉稳有力。
“舒杰那孩子,”李牧忽然说,“和何墨真是亲兄弟一般。”
唐渊点头:“他们一起长大十六年。”
“听说何靖当年救了舒杰?”
“是。舒杰说过,安铁勒屠村,他是唯一活口。何靖将军把他带在身边,当亲儿子养。”唐渊顿了顿,“所以舒杰对何墨……不只是兄弟,更像家人。”
李牧沉默良久,才道:“这雁门关上,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东西。”
“沈薇今日到。”李牧说,“你接待一下。除了你们四个和我,关内没人认识她,别让人说闲话。”
“是。”
唐渊退出帅帐时,舒杰正好练完戟回来,满头大汗。
“唐兄!”舒杰抹了把脸,“听说沈姑娘今天到?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
舒杰嘿嘿笑:“陈巧那丫头说的。她听何墨提过——哦不对,是我跟她提过。”他挠挠头,“去年在长安,我跟她讲过死亡沙漠的事,讲过沈姑娘。”
唐渊看着他:“舒杰,你希望何墨和沈姑娘……”
“我当然希望!”舒杰脱口而出,又压低声音,“我哥太苦了。何叔没了,月儿没了……他总得有个念想。”顿了顿,“而且沈姑娘人好,武功也好,配得上我哥。”
他说这话时,眼神认真得像在讨论军国大事。
唐渊笑了,拍拍他肩:“那就好好接待。”
两人并肩往南门走。路上遇到杨万,他正检查弩机,左手虚握着,右手熟练地上弦。
“杨万,一起去接沈姑娘?”舒杰问。
杨万抬头,眼中闪过一丝波动,点了点头。
—
弩营设在关内东南角。
杨万回到自己帐中,从怀里掏出那枚银铃。铃身血迹已淡成褐斑,但乌兰刻的那道痕迹依旧清晰——那是她最后用指甲划出的,歪歪扭扭,像初学字的孩童笔迹。
去年六月,鬼门道,雨夜。
乌兰挡在他身前时,银铃从她腰间掉落。杨万爬过去捡,手指碰到铃身,还是温的。
“将军,”亲兵在帐外报,“李将军令,鹰愁涧防务由您负责。两千弩手、五百刀盾已集结完毕。”
杨万握紧银铃,金属边缘硌得掌心发疼。
“知道了。”他声音沙哑,“明日我去勘地形。”
亲兵退下后,杨万将银铃系在弩臂侧面。皮绳打了个死结,确保不会脱落。他举起弩,透过弩臂的望山看出去,银铃恰好悬在视野右下角,像一个小小的、沉默的见证者。
乌兰,他看着虚空,心中默念,帮我守好这里。
帮我守住这座关,这片土。
就像你当年,用身体守住我那样。
二月十五,天色终于放晴。
连日的阴云散尽,露出湛蓝如洗的天空。阳光毫无遮拦地洒下来,照得关墙上积雪闪闪发亮,积雪融化处,雪水沿着砖缝淌下,在墙根汇成一道道细流。
辰时末,关楼瞭望塔上的哨兵吹响了号角。
三声悠长的“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,代表有大队人马从南面官道接近。南门内外,士兵们虽仍在各自岗位,目光却都不自觉地瞟向官道尽头。
何墨、舒杰、唐渊、杨万四人并排站在门前。
这是四个月来,他们第一次四人齐整地迎接什么人。饮马河战后,杨万重伤;黄河渡口,舒杰受伤;雪关之役,四人虽都在,却是各自为战。像这样并肩站着,竟有种久违的恍惚。
“哥,紧张不?”舒杰用胳膊肘碰碰何墨。
何墨面无表情:“有什么好紧张的。”
“啧啧,嘴硬。”舒杰转头对唐渊挤眼,“唐兄,你看我哥耳朵是不是红了?”
唐渊笑而不语。杨万站在最边上,左手虚垂,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弩臂上的银铃。
尘土从官道尽头扬起。
先看见的是两面青色旗帜,旗面绣着金色的眼睛图案——“丝路之眼”的徽记。紧接着,车队轮廓显现:二十辆双辕大车,每车四马,车辕包铁,轮毂钉着防滑铜钉。前后护卫十余骑,灰衣皮甲,腰佩弯刀。
车队正中,一匹白马格外显眼。
马上之人着青衫,外罩玄色斗篷,兜帽未戴,长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绾起。距离尚远,看不清面容,但身姿挺拔如竹,握缰的手势从容笃定——那是常年奔波在丝路上的人特有的姿态。
何墨的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剑柄。剑格处磨损的徽记硌着指腹,微痛。
十六步。他默默数着距离。这是死亡沙漠里养成的习惯——判断安全距离。
白马在十步外勒停。
沈薇翻身下马,动作利落,斗篷扬起又落下,露出腰间佩剑。剑鞘普通,但何墨认得,那是吕奉当年用过的剑,后来传给女儿。
她抬起头。
比去年在沙漠分别时清瘦了些,下颌线条更分明,眉宇间那股子英气未减,只是眼角添了细细的风霜纹路。她左手控缰,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,虎口处缠着一圈细麻布,隐约透出淡红。
受伤了。何墨想。
沈薇的目光扫过四人,在何墨脸上停留了一瞬——极短暂。她眼底闪过一丝如释重负。然后她看向舒杰、唐渊,微微点头致意。最后目光落在杨万身上,停顿,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下。
她记得杨万。去年在死亡沙漠见过,那时他的手还未如此伤重……
“沈姑娘。”唐渊上前一步,抱拳行礼,“一路辛苦。”
沈薇回礼,声音清朗:“唐大人,别来无恙。”顿了顿,看向何墨,“何将军。”
何墨点头,喉结动了动:“沈姑娘。”
很平淡的问候,但舒杰在旁边听得直咧嘴——他太了解何墨了,这声“沈姑娘”比平时语气软了三分。
沈薇又看向舒杰,笑了:“舒兄弟,壮实了。”
“那可不!”舒杰一拍胸脯,“沈姑娘你也……呃,还是那么英气!”
他本想夸“好看”,临时改口,脸却先红了。陈巧在身后士兵队伍里看着,捂嘴偷笑。
最后,沈薇看向杨万。
“杨兄弟。”她说,语气柔和了些,“你……”
她注意到了杨万的左手,注意到了他消瘦的脸颊,注意到了弩臂上系着的那枚银铃。但她没问,只是点了点头:“平安就好。”
杨万嘴唇动了动,没发出声音,只是微微颔首。
李牧此时从关内走来,众人让开道路。老将军打量沈薇,眼中露出赞许:“沈姑娘,去年一别,今日再见,风姿更胜往昔。”
“将军过奖。”沈薇抱拳,“民女奉命押送军需,还请将军查验。”
“不急。”李牧摆手,“一路劳顿,先歇息。何墨——”
“末将在。”
“沈姑娘的住处、货物安置,由你全权负责。”
“是。”
沈薇看向何墨,唇角极轻微地弯了弯:“那就有劳何将军了。”
两人目光相接,一触即分。但舒杰看见了,何墨耳朵真的红了。
—
车队入关,在仓库前排成长龙。
卸货时,沈薇亲自指挥。她对物资调配了如指掌,甚至连关内仓库的通风、防潮细节都考虑周到。何墨带着军需官清点,两人配合默契——死亡沙漠三个月,他们早已习惯这种协同。
“药材放东库,那里干燥。”
“皮革先通风,三日后再裁剪。”
“盐铁分开放,铁器忌潮。”
沈薇话不多,但句句要害。何墨偶尔补充:“火油单独存放,远离火源。”“西域的止血散药效猛,用量减半。”
舒杰和唐渊在旁边帮忙,杨万也默默搬着一箱箭镞。他右手有力,左手只是虚扶,动作却稳。
午后阳光西斜时,货已卸了大半。
沈薇走到一辆车前,掀开油布,露出几个特制木箱。箱盖上有火焰徽记。
“火油?”何墨走过来。
“嗯。吐火罗国弄来的,比中原的黏稠,燃得更久。”沈薇拍了拍箱子,“这批不算在清单里,是我个人赠予。”
何墨沉默。火油珍贵,在西域也是紧俏货。
“你不必如此。”他低声说。
沈薇转头看他。两人隔着三尺距离,她能看清他眼角新添的一道浅疤——那是雪关之役留下的;他能看见她虎口麻布下渗出的淡淡血渍。
“何墨,”她叫他的名字,声音轻了些,“饮马河和雪关两场大战,辛苦你了。”她顿了顿,“这些火油,就当是……我的奖励。”
说完,她转身继续指挥卸货,耳根却悄悄红了。
何墨站在原地,左手无意识按了按左肩。旧伤处隐隐发热。
最后一批货卸完时,沈薇擦了擦额角的汗,目光扫过众人,忽然问:“乌兰姑娘呢?怎么没见她?”
话音落下,仓库前的空气骤然凝固。
舒杰搬箱子的动作僵住。唐渊握册子的手紧了紧。杨万背对着所有人,肩膀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
何墨闭上了眼睛。
沈薇怔住,看看这个,又看看那个,最后目光落在何墨脸上。她忽然明白了,脸色瞬间苍白。
“她……”沈薇声音发颤,“什么时候的事?”
“去年六月。”舒杰低声说,放下箱子,走到沈薇面前,“鬼门道……她为了救杨万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,但沈薇懂了。她记得乌兰,记得那个草原姑娘明亮的眼睛,爽朗的笑声。记得她在死亡沙漠里说“等打完仗,我要去江南看花”。
沈薇踉跄一步,扶住身旁的车辕。手指抠进木头,指甲泛白。
“怎么……怎么会……”她喃喃道,眼眶红了。
唐渊走过来,轻声道:“沈姑娘,节哀。乌兰姑娘她……走得很英勇。”
“英勇?”沈薇忽然笑了,笑容比哭还难看,“她才十九岁……她还说想去看江南的春天……”
她说不下去了,低头捂住脸。肩膀微微颤抖。
何墨走到她身边,沉默地站着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——这半年来,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乌兰的死。只是每个深夜,都会想起那个雨夜,想起乌兰最后看杨万的眼神。
那么温柔,那么不舍。
杨万终于转过身。他脸色惨白,左手不自觉地蜷缩着,右手紧紧握着弩,指节泛白。弩臂上的银铃在夕阳下泛着暗淡的光。
“沈姑娘,”他开口,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,“乌兰她……提起过你。她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子,说她羡慕你能走那么远的路。”
沈薇抬起头,泪痕满面。
杨万从怀里掏出一块叠得整齐的布帕,展开——里面是一小撮干枯的野花,早已褪色,但依稀能看出曾是紫色。
“这是她在鬼门道采的。”杨万说,声音更哑了,“她说……紫色是草原上最好看的颜色。她说等春天来了,要采更多,编成花环。”
他把布帕递给沈薇。
沈薇接过,手指轻抚那些干枯的花瓣。泪水滴在上面,洇开深色的斑点。
五人沉默地站在夕阳里。仓库前的空地上,影子拉得很长,交错在一起。
远处传来士兵换岗的号令声,炊烟袅袅升起,关内渐渐飘起饭菜香。生活还在继续,战争还在继续,只是有些人,永远留在了去年六月那个雨夜。
许久,沈薇擦干眼泪,将布帕仔细叠好,收进怀里。
“乌兰,”她对着北方轻声道,“姐姐来了。”
接风宴设在帅帐旁的小厅。
菜是军灶做的,实在:烤羊、炖肉、烙饼、腌菜。酒是太原府送来的汾清,藏在窖里半年。
气氛却有些沉。
沈薇换了一身素青棉袍,头发简单束起,眼圈还微红。她坐在李牧左侧,何墨在她对面,舒杰、唐渊、杨万、陈巧依次落座。
李牧举杯:“沈姑娘,敬你千里运粮之义。”
沈薇起身,双手捧杯:“将军言重。民女只是做了该做之事。”一饮而尽,面不改色。
舒杰想活跃气氛,说起去年在长安追查王玹余党的趣事——当然是美化版。说到他们如何闯刑部,如何与官兵交手,陈巧在旁边小声补充:“舒大哥当时一脚踩进粪池,臭了半身。”
舒杰脸一红:“丫头,又揭短!”
众人都笑了,气氛稍缓。
沈薇也笑了,但笑意未达眼底。她目光不时瞟向杨万——他几乎没动筷子,只是偶尔抿一口酒,左手一直垂在桌下。
“沈姑娘,”李牧问起正事,“这批物资之后,下一批何时能到?”
“三月中旬。”沈薇收敛心神,“我之前在西域各国有不少旧识,已联络妥当。药材、皮革、铁器都能持续供应,只是粮草……还需中原筹措。”
唐渊点头:“江南那边,蒲姑娘已在准备。只是最近太原府至雁门关的粮道不太平,已有两批粮草被劫。”
沈薇皱眉:“什么人干的?”
“说是山贼,但尸体刀伤整齐,是军队制式刀法。”唐渊压低声音,“我怀疑是王玹余党与地方驻军勾结,断我们粮道。”
舒杰一拍桌子:“又是这帮杂碎!前线拼命,他们在背后捅刀!”
“慎言。”李牧瞪他一眼,却无多少责怪之意,反而叹息,“这就是为什么沈姑娘这批物资如此重要——若我们真虚报兵力,何需这么多军需?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”
沈薇沉吟片刻,道:“将军,我在长安有些生意上的朋友,消息灵通。据他们说,王玹虽已投奔北莽,但朝中党羽未清,且……”她顿了顿,“似乎与江南某些世家有牵连。”
唐渊眼神一凛:“江南?”
“是。王玹当年推行新政,触动了江南世家的利益,按理该是死对头。但最近半年,有迹象表明,某些世家在暗中向北方输送物资——不是给朝廷,是给谁,不得而知。”
何墨忽然开口:“王家在江南有产业?”
沈薇点头:“王玹的妻族是润州林家。而且……”她看向唐渊,“蒲姑娘在江南筹措粮草,恐怕已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。”
唐渊握紧酒杯。蒲英儿信中从未提过这些。
“多谢沈姑娘提醒。”他郑重道。
李牧举杯:“这些事,暂且放一放。今夜只喝酒,叙旧。”
众人举杯。舒杰又开始讲黄河渡口一战,说他如何一戟挑飞三个黑衣人。陈巧小声说:“然后就被箭擦伤腿,躺了半个月。”
“那是意外!”舒杰争辩。
气氛终于活络起来。连杨万也微微弯了弯嘴角。
宴至亥时,李牧先去歇息。唐渊送沈薇回住处——那是临时腾出的小院,原是个书吏住所,虽简陋但干净。
何墨独自走上东侧城楼。
夜风寒冽。关墙上火炬摇曳,将人影拉长又缩短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,很轻,但他认得。
沈薇走到他身侧,也凭栏而立。她换了身素青棉袍,外罩狐皮斗篷,头发散了下来,只用一根发带松松束着。
“怎么没去休息?”何墨问。
“睡不着。”沈薇望着关外,“想到乌兰……想到这关外不知有多少人想踏平这里,就睡不着。”
何墨沉默。半晌,道:“你要留在军中?”
沈薇转头看他,月光照在她侧脸:“你以为我是为你来的?”
何墨语塞。
沈薇却笑了,笑容里有疲惫,也有坦然:“何墨,我确实担心你。但更大的原因是,‘丝路之眼’不能倒。而保住‘丝路之眼’的唯一方法,就是保住雁门关。”她顿了顿,“所以我来了,带着能带的所有物资,做我能做的一切。”
何墨点头。这才是沈薇。
“那你呢?”沈薇反问,“你真要留在军中?朝廷如此对你父亲,对你,你还要为他们守关?”
何墨握紧栏杆,木刺扎进掌心。
“我不是为朝廷守关。”他声音低沉,“是为我爹,为月儿,为乌兰,为死在关外的百姓,为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为那些相信我,跟着我的人。”
比如乌衣营的老兵,比如舒杰,比如唐渊,比如杨万。
比如……她。
最后半句他没说出口,但沈薇听懂了。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“何墨,”她忽然说,“若此战结束,你还活着……你会继续做官吗?”
何墨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望向南方,那是中原的方向,也是长安的方向——那里有他父亲的冤案,有他妹妹的孤坟。
“不会。”他诚实地说
沈薇看着他。这个男人二十六岁,却已背负了太多。父亲冤死,妹妹病逝,并肩的战友死在眼前,自己一身伤病,还要扛起一座关的存亡。
“何墨,”她轻声说,“我们的约定…”
何墨转头看她。
月光下,沈薇的眼睛清澈坚定:“我先陪你守这座关。等守住了,如果你还想去找龙城……我陪你。”
这是承诺,比任何情话都重。
何墨喉结动了动,千言万语堵在胸口,最后只化成两个字:“……好。”
沈薇笑了,这次笑意直达眼底。
低头,她忽然瞧见了何墨腰间那枚刻着“薇”字的玉牌,红绳已洗得发白。
她双颊一红。
“沈薇,”何墨忽然说,“虎口的伤……记得上药。”
沈薇一怔,抬手看了看虎口麻布,笑了:“你看见了?”
“嗯。”
“小伤。路上遇到马贼,弯刀震的。”
何墨没说话,只是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瓶,塞进她手里:“军中药师配的金疮膏。”
沈薇握紧瓷瓶,瓷壁还残留着他的体温。
远处传来三更梆子声。
“我该回去了。”沈薇说。
何墨点头,陪她走下城楼。到小院门前时,沈薇忽然转身:“何墨。”
“嗯?”
“舒杰跟我说了饮马河的时候…。”她声音很轻,“对不起,那时候我不在。”
何墨摇头:“都过去了。”
“没过去。”沈薇看着他,“我只是想说……以后,我在。”
说完,她推门进院,没回头。
何墨站在门外,良久,才转身离开。月光将他的影子投在青石路上,拉得很长,很孤独。
但这一次,他知道路的尽头,有人在等他。
—
小院厢房内,沈薇坐在灯下,展开杨万给的那块布帕。
干枯的紫色野花静静躺在帕心。她想起去年在死亡沙漠,夜里乌兰曾指着远方的沙丘说:“沈姐姐,你看那像不像我们草原上的山?等不打仗了,我带你去草原,那里六月的时候,满山都是这种紫色小花。”
那时乌兰的眼睛亮晶晶的,满是憧憬。
沈薇轻轻抚过花瓣,泪水无声滑落。
“乌兰,”她对着灯火轻声道,“你看见了吗?何墨还活着,舒杰还活着,杨万……他还活着。”
窗外,二月寒风呼啸而过,卷起檐下残雪。
春天就要来了。
战争,就要来了…